|
(林毓生《中国意识的危机》)当一个鲜活的生命被倾轧掉人的“水分”,退守到“物”的范畴,他的行动就如同舞台上的道具,便会被别人随便搬来搬去,抛来抛去——这在冷漠无聊而又麻木残酷的看客看来,的确是生动而有趣味的事件。
“天地不仁,以万物为刍狗”(《老子》),世界是不会偏爱某一个人的。只有认识到自己的生存困境,自觉自身的生存现状,就是争取到了做人的权利。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曾说,周围世界总是肮脏的、令人“作呕”的。而阿Q存在的那个世界,岂止肮脏得令人“作呕”,简直是让人“深恶而痛绝之”的,用阿Q自己的口头禅说:真是太“妈妈的”了。阿Q在它面前显得无疑是太渺小、太苍白了。如果说世界真是个大染缸,阿Q绝不可能有荷花的坚贞与自怜(他不可能像屈原那样“清醒”,时时企图求得自救),其实,他本身就是一只全黑的乌鸦,所以玷污与堕落是于他毫无相关的事情,痛苦又何以产生?即便如此,我们的阿Q还是有幻想的:“威福、子女、玉帛”——“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——罢了。”(鲁迅《热风》)幻想,有时简直表现为不着边际的荒唐与可笑,幻想的结果势必使其陷入更深的“虚无”。阿Q的“虚无”还表现在他的自轻自贱上,比如他被别人痛打时,承认自己是“虫豸”以示弱,但往往又唤不起别人的恻隐之情、同情之心,即便如此,他也毫无羞恶之感,他总会为自己开脱,常常以幻想的“胜利”来安慰自己,最后,他的精神总是“胜利”的。“精神胜利法”本身就是一种虚幻存在。尽管有“谈阔”被嘲,“恋爱”失败,“革命”不准等一系列“非人”待遇的刺激,但也无法激活其早已迟钝了的神经末梢,从而使其感受到自己“不人”的痛苦。
阿Q的“我在”还混杂于“他在”之中,即他根本没有把自身与周围世界区别开来,“自我”与世界的界限是那么的暧昧与模糊,以至于认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,所以,他并无孤立之感。他不能意识到自己正面临着“作为世界的世界”,即在自己之外还有一个外在世界的作用与制约。他既没有了爱,也就无所谓恨了。从这一方面讲,阿Q是真正孤独的,但他对这种孤独的不自觉,则构成了悲剧。
上一页 [1] [2] [3] [4] [5] 下一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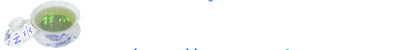
上一篇文章: 《人在高三》作文讲述
下一篇文章: 从“发微”谈《剃光头发微》的构思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