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
精神作为一种“存在”,一种意识形态,一种普遍存在的集体的民族无意识,其深度其广度却是难以估量的。
阿Q作为一个“个人的存在”,上无片瓦,下无寸地;他没有家,没有亲人,没有朋友,没有固定职业,连自己的姓氏、名字、籍贯都失去了。他失去得太多了,以至于成了没有标签,没有命名,没有包装,没有来路,没有归途的“物性存在”。他“赤条条来去无牵挂”,他与世界(他人)的关系朴素简单到几乎纯粹的地步。他总是飘飘然地飘来飘去,他的生命始终处于一种无名无状的无根状态。也许他生命中有不能承受之“轻”,但他始终不自觉,所以他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无法真正体验到此时此境的“这一个”、我的、个人的真实存在。“一切现实的东西,其对我们所以为现实,纯然因为我是我自身。”(雅斯贝尔斯《生存哲学·导言》)没有个人的存在,其他一切事物就不可能成为真实的存在,就会成为没有意志的虚无。阿Q既不能感知自己的存在,也就根本不能超越自己,或者根本不懂得超越自己,他只能是一个混沌一团的,抽空了内质的,被作者刻意设计的,代表大众生存的艰涩的符码。因此,他也就根本无法自觉地掌握自己的命运。他的一颦、一笑,一举手、一投足,他的所有行动与思想,都必须受角色的框禁,他不能僭越自己的应然角色而“自由地生存”。阿Q必须始终处于麻木的不自觉的混乱状态之中,因为他是作者“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”(鲁迅《伪自由书·再谈保留》)集大成者。这里的阿Q不再是一个具体确定的“我在”,而是各个“我在”的混合体,如同一个傀儡,在作者的操持下,演绎着国民的种种劣根性。因为,他本来就是一个“模特儿”,而“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,看得多了,凑合起来的”(鲁迅《二心集·答北斗杂志社问》)。“依存在主义者看来,所谓人是指一个具体的个人,不是一个抽象的认识主体。”(考卜莱斯顿《当代哲学》)恰恰相反,阿Q就是这样“一个抽象的认识主体”,他存在的实际意义就只剩下演绎作者的抽象思想,除此以外,即无意义。这里的关键词还是“演绎”,是舍掉了“人”的具体内涵的程式化的表演,“马戏”的意味就很浓。鲁迅先生企图从生物本能的意义上“演绎”“人”的退化(物化)过程,以及人面对退化所做的种种无意识的挣扎,以及挣扎而又无所改变的悲哀,以及悲哀而知者的苍茫的凄凉与厚重的孤独。“如果我们把阿Q通过社会所获得的传统社会文化体系的因素,也包括进去作为他的本性的部分,那么,阿Q便可以称为几乎全靠本能生活和行动的动物了。” 上一页 [1] [2] [3] [4] [5] 下一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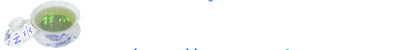
上一篇文章: 《人在高三》作文讲述
下一篇文章: 从“发微”谈《剃光头发微》的构思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