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
怀疑与激变
张炜
——解读毕加索
面对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强悍茁壮、伟大的狂放的艺术家,我们常常只有惊叹。其他都是惊叹之余,是曲终之后的惋惜与回味,或许还有细细的咀嚼——品咂之中的苦味和甘甜,以及感涩。
在人类的历史上,有一些艺术家是难以超越的,他们本来就是这样一些强大特异的生命。这些生命仿佛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,一生可以纵横涂抹而不知疲倦。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拥有一个长长的生命、漫漫的创造历史:从很早即开始起步,直到最后才缓缓终止。毕加索最早的作品是十岁左右画出的,如十四岁的《裸脚女孩》、《老渔民》等杰出的作品——仅此一条就决定了这是一个非凡的绘画天才。这人稚嫩的生命竟然对人生和世界的苦难、对世间奥秘知道得那么多那么早,这难道仅仅是“学而知之”吗?面对这样的人物,我们使用惯常和耳熟能详的、已有的那点儿知识和经验去加以解释,够用吗?
纵观他一生的无数作品,可以从中找到各种风格倾向各种情绪,这些奇迹领略不完也诠释不尽。它们本身即组成一个宇宙,其中繁星闪烁,风云变幻,既有风和日丽也有雷鸣电闪,更有惊涛骇浪,那种动人的美,让人过目不忘的最为独到的呈现与表达,简直比比皆是。我们可以一口气列举出《站在球上的孩子》、《特技表演者的家庭与孩子》、《奥尔喜肖像》、《持扇的女子》……多到一时难以穷尽。最伟大的艺术家,他们的心底从来都是充斥了不安:怀疑自己的意义、自己的创造、自己的人生道路,这种怀疑的结果就是艺术生涯中的无数次激变,是无头无尾的探求,大嬉戏和大玩笑,包括大绝望大痛苦;还有恶作剧,装傻与佯疯,傲世与自卑,欺世与自欺……这一切综合一起,让后来人去清理和辨析,去极为困难地分拣。后来人常常是不知所措的,在这亘古未见的一大堆斑驳灿烂面前,大半只有叹息,而没有能力去鉴别——他们甚至在这样的生命面前连起码的冷静都要丧失,视听失灵,这就是艺术家和受众的双重悲剧。这种悲剧正没有个终止。毕加索的悲剧正没有个终止。
有人不止一次指出他是现代绘画史上的“巨灵”,除了“野兽派”以外,几乎开创了所有潮流的先河。这似乎是一个事实。但所谓的“潮流”和“流派”就真的那么重要吗?是的,它们使当时和后来的艺术处于激活状态,它们也使各种尝试变得可信和可能。但当我们面对一大堆千奇百怪、巧思百出,有时直接就是丑陋怪异到目不忍睹的东西时,难道不应该产生一些怀疑吗?
是我们错了还是当年的大师错了?追问的结果是:大概谁都没错,是时代错了。在一个人类正被物化、异化,正在走入失去自我的现代荒漠的时代,作为个体,一个生命,你尽可以呼号,但没有回音,更没有应答……至此,我们或许可以稍稍窥见毕加索当年的伤痛。面对那样的时代,人们所能做到的大概也就是像当时的大师那样,做下这疯癫无忌的大喧哗和大游戏了。他要可意地尽情地嘲讽一番,既嘲讽自己,又嘲讽时代;既嘲讽去者,又嘲讽来者。因为不如此就不足以表达心中的全部感触、百缠纠结无从摆脱的矛盾与痛苦。最盛的生命力,最深的牵挂,最长的忧虑,还有最强的悟性——就是这样的一个人,他一旦面对着捉弄人的上帝,又能怎样呢?
不仅如此,他还要面对一个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时代,特别是一个虚荣的时代。看来—个艺术家被逼到了尽头,就偏要穿上皇帝的新衣,偏要以此为乐——他与另一些人的不同就在于他的自觉与清醒。毕加索兴之所至任意涂抹,像儿童一样嬉戏不休,上下游荡,四方徘徊,进入化境般的流畅自如,实际上却是隐含了一个生命的全部悲凉无告。这儿有泪水,有傻笑,更有绝境的哀求,在他这儿等于是以歌当哭。一个天才的生命在大限面前,在那个残酷的必要来临的狰狞面前,也只有报以相同的狰狞——不,是鬼脸,是苦笑,是喜上眉梢的大快意。
就最后而言,就其背后的意义来说,毕加索是消极的。
他没有将一个人追求完美的努力、将这种生命的搏斗进行到最后。他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屈服。我每一次看到他的不可征服的创造,就在心里悄悄发出叹息:伟大的毕加索,屈服的毕加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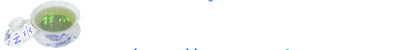
上一篇文章: 爆笑奥运主持人语录集锦
下一篇文章: 阅读:只有扇子崖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