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
作一个小测试:您会认为一截磨损的电线更恐怖还是一条活体的蛇?我觉得是后者。而实际上,破损电线对现代人造成的伤害要猛于蛇。
可是为什么我还是会觉得蛇是更危险的致命物呢?这是因为蛇对我们祖先造成的惊吓要远甚于磨损的电线,后者在人类进化历史中出现的时间太短,其恐惧指数无法在基因水平上表现出来。
人的其他感情也莫不与人类的进化史有关。这就是人本主义的要义。比如说,我们对住宅的选择,有一种回到祖先居住地的本能的渴望,于是,房产企业家用“山水名居”、“花园洋房”这类的人造自然景象来打动消费者,因为我们的祖先居住在大自然中。在这样一种倾向的支配下,城市的发展如同一棵大树,树龄越长,中心越空:郊区离自然近,郊区的房产成为富人的首选,也是绝大部分城市人心仪的目标,城市中心的人气指数越来越低。
借用一下古巴比伦空中花园的思路来改造一下我们的城市如何?把城市的交通全部“沉入”地下,把城市的高楼全部披上植物,把城市的地面全部种草种树,变成非洲热带稀树大草原那样的景观,这样,我们从城市的建设物里进出,犹如山顶洞人进出他们的洞穴。我们离自然也近似地像山顶洞人挨得那么近,我们的城市就像避免大树那样的空心。
阿西莫夫写了一本名叫《钢窟》的科幻小说,其中是一个全由地下城市构成的世界。把地面腾出给其他动植物,这样,乡村就近在咫尺,即只在地下城市水平面上几百码的地方,自然界只隔着一部电梯的距离。日本正在考虑阿西莫夫的设想,有些项目已进行规划。这一切都可以从渴望回到祖先居住地的本能中获得解释。对钢筋水泥建造的城市,可以通过塑料疏导板和人造土壤,把任何一座建筑的前后左右上五面全部披上绿装,而且造价仅是建层本身造价的千分之五。这可以让我们的建筑获得山洞那种部分的好处,比如山洞的温度比较恒定,远离噪音。
如果我们真的不想让城市“空心”,而一时又不能发展地下城市,就去建立空中花园吧。这并不是科幻,而是可以立即着手进行的事情。我们完全能对现代版的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给予期待。
15、成龙到北大讲课
明星与大学向来是媒体关注的焦点。10月17日成龙在北京大学刚讲完课,媒体就争相报道,虽然题目和侧重点各异,但成龙的一段话都没有省略:你们知道我是你们的荣誉教授吗?之前一直请我来讲课,我打马虎眼就过去了,其实我不是不想来,而是不敢来。北大即使不属于全世界一流的学府,在中国也是数一数二,我来干什么?你们都是大学生,我连书都没有读多少。任何一个在座的人的学问都比我的好。
在担任北大荣誉教授之前,成龙是香港院士、博士、荣誉教授,还去剑桥、哈佛用JackieChan(成龙的英文名字)的破英文教过课。
由成龙的话,可以引出另外一个话题:谁有资格到北大讲课?
很早是周星驰,今年又有刘镇伟、李连杰相继到北大讲课。查阅相关的新闻就会知道,媒体曾把他们到北大讲课上升到大学精神沦落与否来讨论,而且多持批评态度,认为北大利用演员的知名度作秀,成了明星的后花园和娱乐场所,是大学精神的沦落。不单影视明星,和通俗沾上边的金庸和李敖到北大讲课,也遭到过铺天盖地的非议。
一个没读过多少书的演员到中国数一数二的学府讲课,从学术角度讲,意义确实不大。然而,大学教学生的仅仅是学术吗?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非常经典地解释过:“大学者,有大师之谓也,非谓有大楼之谓。”大学是智慧与博大胸怀的代表,不应是大楼、自大的代表。
北大的校训原来是“学术自由,兼容并包”,后来改为“爱国进步民主科学”,清华的校训是“自强不息,厚德载物”,上海复旦大学的校训是“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”。这都说明“大学精神”的核心是兼收并蓄精华。
成龙到北大讲课,正是体现了大学的精神。我们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有多少人能够取得成龙、周星驰和金庸、李敖的成就?又有几人能如成龙那样满世界穿着唐装传播中国传统文化?成龙本身就是一本教材,他的人生之路并不平坦,其中的艰辛、坚强和博爱以及民族精神,的确值得大学生们借鉴。
16、别的名字
就像中国人以前自报家门叫“燕人张翼德”和“常山赵子龙”一样,我们熟悉的“达·芬奇”,其实是“芬奇镇的列奥纳多”。
一定有些什么,是我们不能言说的东西,从时间的缝隙里和万物一起滋长出来,界定了人们的常识和经验。比如说一个名字,当你知道他叫这个名字的时候,你知道他在别的地方、别的时代,有人叫他别的名字吗?
就拿达·芬奇来说,研究意大利文学的吕同六先生,叫他“芬奇镇的列奥纳多”。因为“达”在意大利语里是“在”的意思,“芬奇”则是意大利的一个小镇,也就是达·芬奇本人的出生地,而达·芬奇的全名是“列奥纳多·达·芬奇”,于是,就像中国人以前自报家门叫“燕人张翼德”和“常山赵子龙”一样,我们熟悉的“达·芬奇”就变成了“芬奇镇的列奥纳多”。
可是约定俗成,如果达·芬奇改名叫“列奥纳多”,我会在第一时间想起《泰坦尼克号》男主角的名字莱昂纳多·迪卡普里奥,而不是别人。网上有台湾网友谈论两岸的翻译,说台湾的“梵谷”到大陆变作“凡·高”,好像就成了普通人———如果都这样望文生义的话,大陆的“达·芬奇”,到了台湾变“达文西”,是不是就失却了他旷世少有的磊落英奇了呢?据说这位大画家可是文武双全的哦,单手便能掰断一只马蹄铁。
罗密欧与朱丽叶,上世纪30年代有旧译叫做“柔蜜欧与幽丽叶”,既“柔”且“幽”,不光“丽”,而且“蜜”,在当时可谓非常之鸳鸯蝴蝶而罗曼蒂克,是很新派的事。可是放在今天,却怎么看怎么觉得外国人不像跟我们用同一种材料做的,倒像是菠萝蜜一般的水果,或者,至少也是幽兰护肤霜之类。
阳朔西街,清康熙年间便已得名,民国时期赶时髦,改名叫“西马路”,可能那时候“马路”是一种大都市里才有的东西,说出来会比较铿锵有力,比如要是有人一拍胸脯说“我到过上海的四马路”,蒙蒙小地方人,还是很有气势的。同一条西街,“文革”时改名叫“东风路”,表示要以“东风压倒西风”。这种荒谬的更名事件,在当时全国许多地方都发生过,之后的事大家都知道了,又一起改了回来。
以上说的是由于地域和时间的不同,而造成的人们对名字接受上的差异。也有完全因为断句理解不同,说出来的名字就有天壤之别的,比如外地人到北京,会把“东四/十二条”断作“东四十二/条”———北京可真大,光东边就有四十二条!再比如外地人买苏州名优特产“真正/老/陆稿荐”的酱汁排骨,不知“陆稿荐”是一老字号,容易断成“真正/老陆/稿荐”,“老陆”反正是一了不起的创始人,以为这一点毫无异议,以为“稿荐”跟“推荐”沾点边,殊不知它在苏州话里,是“草垫”的意思,而“老”是正本清源,廓清所有冒牌货。
名字这东西,习惯成自然,是一种文化的鲜活表征。即便是在名字这么小的事上,有时候有了分歧都难以互相说服,更何况其他。赛珍珠写她旅居中国数十年的“异邦客”母亲时说过一句话,大意是说,一个人要属于一种文化,必须与它同生共长,容不得半点抽离。如今东奔西走的人多了,不时的“抽离”常常在所难免,知道达·芬奇叫达·芬奇,也不排除人家有时候在有的地方叫叫别的名字。
17、有用的猫
有一户人家的母猫生了三只小猫。三只小猫断奶后,憨态可掬,招人喜爱。附近的人听说有猫仔可抱养,纷纷前来询问。不久,便被抱走一只。这天中午,我在门口乘凉,正好碰到一老汉来看猫仔。
老汉,精短身材,脸色红润,精神抖擞。母猫带着两只小猫在方桌下纳凉。老汉在征得人家的同意后,凑近小猫细细观察。他先是用手势逗小猫玩。体壮灵活的小花猫摇头摆尾,一双骨碌碌的眼睛煞是可爱;那只小白猫对人爱理不理。老汉用手疼爱地抚摸小花猫,顺便吹了几声口哨,并赞不绝口。小花猫挺会招人疼,一跳一跃,颇有几分下山老虎之势。老汉又把注意力转向小白猫,可他伸手向小白猫示好时,小白猫“喵”的一声,并不买账。老汉脸色不悦,嘟了一句“丑东西”。老汉又拿起一块鱼骨头喂两只小猫,小花猫很开心,小白猫仍然爱理不理,显得十分懒怠。
老汉抱起小花猫,亲手喂鱼,甚至亲了小花猫一口,喜爱溢于言表。末了,老汉对主人说:“我要小白猫!”众人疑惑不解,老汉也不多说。
旁边有一个小饭店,几杯米酒下肚,老汉的话闸拉开了:“本来,今天我并不打算要猫的。猫生仔,一龙二虎三猫四老鼠,越多越没用。白天活跃的猫,晚上贪睡。傲气的猫,与人保持距离。贪吃的猫,鬼才信它会捉老鼠呢……”我恍然大悟。
末了,老汉丢下一句话:“我不喜欢小白猫,但它有用。”
18、取而代之
几位汽车司机在一起谈论恋爱、婚姻、家庭,不约而同都以轮胎来作比拟。
司机甲:我看中了我们公司一位靓女,天天发短信给她,向她表露自己的爱慕之情,可她置若罔闻。这好似在一辆行驶的车上,她是前轮,我是后轮,追呀,追呀,后轮总是追不上前轮。
司机乙:我们结婚了,建立了家庭,共同承担家庭生计大事。这好似在一辆大卡车上,我们是一对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双轮胎,共同负担大卡车分配的载重任务,共同为驱使大卡车行驶而飞转。
司机丙:我们离婚了,这好似原来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双轮胎脱轴了,一个飞向东边,一个飞向西边。
司机丁:我们的婚姻中出现了第三者,这第三者好似挂在车辆后面的备用胎,瞪着眼睛觊觎着我们,总想把我这个“轮胎”排斥出去好取而代之。
19、坚持下去
上世纪70年代,美国癌症研究专家朱达·福克曼提出了一个大胆想法:肿瘤细胞需要血液提供营养。如果没有血管,癌细胞得不到血液供应,肿瘤就会缩小乃至消失,就不会对人或动物构成危害。经过多年潜心研究,他据此制出了血管生成抑制剂。如今,有很多癌症患者受益于这个研究。
但在朱达·福克曼首次提出肿瘤新学说时,医学界的主流观点是,肿瘤不能诱导身体产生供应肿瘤营养的新血管。专家们认为他的想法是异想天开,毫无价值。但福克曼却几十年都投身于这个领域的研究。其间,他受到了同行无数次的怀疑与奚落。
在朱达·福克曼名气越来越大、研究成果得到认可时,他已经独自寂寞地耕耘了35年。福克曼说过的一句话是:“坚持与固执不同,我选择了一个值得钻研的研究领域,然后始终不渝地坚持下去。”
20、不能放下
饱受疾病折磨的史铁生以《病隙碎笔》荣获今年的鲁迅文学奖散文奖。他在颁奖后说:“困境的本质对于人的伤害是一样的,如果不去寻找生命的意义,生命就没有意义。”
史铁生今年55岁,21岁因病致残,在轮椅上度过了30多年。他却写出了知青题材短篇小说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、哲理性长篇小说《务虚笔记》、散文《我与地坛》等优秀作品,分别获得过1983年和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。
这个顽强的汉子,近几年又得了尿毒症,肾也随之衰竭,时刻都徘徊在死亡边缘,写作变得极其困难。这次获奖的《病隙碎笔》,前后写了4年,有时一天只能写几行字。一般人看来,这样的遭遇和经历,一定是痛苦而又悲伤的。但史铁生却非常乐观。他说:“把悲观认识清楚了就是乐观。”因此,这个坐轮椅的汉子总是笑容满面,甚至有人说他是中国最爱笑的作家。
史铁生说:“生病算是一项别开生面的经历。”由于疾病,他一星期要去医院透析3次,由于贫血,缺氧,没有力气,他有时觉得自己可能写不了了。这时,支撑他创作的力量完全来自于意志,因为他意识到:“不能放下,否则可能就彻底放下了。
上一页 [1] [2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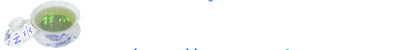
上一篇文章: 备考推荐阅读最经典的报刊搜集作文素材300篇九
下一篇文章: 备考推荐阅读最经典的课文抒情精美范文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