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
韶华易逝,流逝如掌中沙的是年轻的光景;然而,青春却可以长驻,保持不朽的是一种昂然的生命力,绽放的乃是生命之春的盎然气象。
光阴流转中,多少人失却了直面人生秋冬萧索的勇气。张爱玲晚年高群索居,三毛断然选择结束生命,连李敖这般强韧的人也曾扬言:“若再也说不出话,将垂垂老矣的我扔到海岛上吧。”他们所畏惧的、急切逃避的,便是现实中的“青春不再”……不复浪漫,不再强悍。殊不知,岁月会侵蚀身体,但是只要心不老,时光永新,青春亦可长存。
奥地利作家托尔斯曾歌颂过:抚平心灵的皱纹,等同于青春永驻。
在时光的潜网中,没有谁能逃脱自然的规律;但在心灵的空间中,乘长风、万里溯流而上者并不鲜见。画家黄永玉古稀高龄,仍以“流浪者”的心态对待名利,以“冒险者”的姿态广泛尝试多种艺术领域,不断发掘新奇。同样,齐白石晚年仍不懈追求画艺的提升,多次改变画风,终达登峰造极的境界。诗人席慕容步入老年后,每每与青年人畅谈文字,那眼眸里闪烁的光芒仍告诉我们:那是一位满怀诗意的女子。
美人会迟暮,但眼神中的光彩不应湮灭。华年会消逝,但激扬活力的青春不应褪色。
当我们一次次阅读那些名诗、欣赏那些名画时,我们分明在触摸一颗颗跳动的心,那么有力,那么张扬,也许它们的创作者已经离去,但我们坚信会有另一批朝气蓬勃的来者接过其衣钵,成为人生的新歌者。
我想,这是深植于我们血脉中对美对青春的认同。这份敬与爱,犹如一根细而长的线,将我们一颗颗珍珠串连起来,熠熠生辉。
抛开童稚、拥抱青春的我们,不妨在心间种下青春吧,看着自己有刻度地成长,拥有一片浓荫,撑开无限春天。
薄暮依旧炒米香
夕阳笼罩下,村口一片静谧安宁。橘红色的阳光渗过茂绿枝叶间的缝隙,在天地间洇出一幅金灿灿的油画。
我又一次迈进村子,却再也辨不出曾经的痕迹。村口的老人们喃喃说道:“扎伞的老王在你走后两三年就死啦,这不,十多年光景,当年那个还吮着指头的你,现在都长成大小伙喽。岁月不饶人哩……”见我欲问,一旁佝偻着背的老太太插嘴上来:“若是说来,你该还记得那炒米师傅吧,喏,再往前走两个巷口便是。”
年幼时的我,恍惚以为村里的所有都是永恒的。可岁月从没有停止她那匆匆的脚步,逝去成了不变的旋律。好在,还有这样一处值得我惦念。
走上前去,三五人群团着的,不须再辨,正是我幼时那位炒米匠。他端坐在不知谁家砌房留下的水泥墩上,正心无二顾地边旋转边望着抓在手上、早已炭黑的葫芦形炉膛。阳光静静地覆在他的额头上。黝黑的额头上沟壑纵横,沁出的细密汗珠簇拥着,反射出迷人的金光,似一抔泥土中散落的金粉。
他的右手正奋力地鼓着风箱,简陋的炉灶上火苗跃动。一旁的小炉灶上支着一口锅,清净的汁液正烧得噼啪作响。细细听来,寰宇间仿佛只剩下火苗炙燃的嗞嗞声。轻轻一嗅,糖汁熔化的丝丝甜意直润肺腑。
炒米匠望着压力表,轻轻一唤:“要炸喽!”平淡中渗出一丝威猛,把一个三四岁的女孩吓得哇哇直哭。炒米匠嘴角轻咧,围观的大人倒是笑得前仰后合。只见他娴熟地把炉膛塞入布箧中,手中一根杵棒猛力一拨,“嘭”地一声,白烟缭绕。那孩子这会儿破涕为笑。脆脆的香气混合着糖汁软软的清甜让人心旷神怡。
趁着热,炒米匠将筷子挑起一丝糖汁,拉伸成一条绵绵的线。火候到了,将糖汁倒入了一旁的浅铁盒,再将新制的炒米倒入,竹篾将混合好的炒米糖摊平,待冷却了用刀切成方块,便成为我童年里最恋恋不舍的美食。
“还是当年那般香呦!”我轻轻吐了一句。炒米匠这才抬头,仔细地凝望着我,愣了好一会儿方才恍然大悟。他笑盈盈地望着我:“还行还行,真没想到你居然也长成这般大了。”我笑问:“如今生意如何?要知道,当年的我可对你崇拜得不行呦。”他似有心思般轻轻一叹:“曾经,我们也以为这手艺会传下去。这才十多年时间,哎……光阴过得真快呀。”
我品出他心中的一丝不舍,悄悄离开,心中萦绕着些许困惑。回头望去,炒米匠和他的活计儿沉浸在薄暮里。
薄暮依旧,炒米香。吆喝声渐渐地,渐渐地,寂了下去。
荒山种茶人
父亲将他的青春奉献给大山。
清明时节,我冒着霏霏细雨,回到了阔别的家乡。
父亲的腰弯得深深的,像是融进了茶园无涯的绿意里。漫山遍野的深绿、碧绿、浅绿直逼我的眼球,又像是给大山围上了一层曼妙的绿纱。
我随着父亲走向茶园更深处,四周涌动着如凝脂般厚重的绿意。任南风带着沁人的土香袭乱我们的头发,那不该被打扰的世界似乎在浅斟低唱,山里的孩子喜爱漫游于山林,趁散放的鹧鸪还未归巢,偷偷寻觅它们下的蛋。夕阳西下,肥嘟嘟的小子用衣裳兜着满满的鹧鸪蛋回家。
还记得,曾经的大山却是一片荒芜,粮食广种薄收。山里的人不希望把青春耗费在大山,纷纷外出打工,父亲却坚定地留了下来,因为,山里的老人和孩子都过得很苦,他不忍心弃他们不顾。
于是,无论四季更替,他在无怨无悔的奉献中,诠释了青春。
春天,他整地,开渠,播种。他惊讶地发现大山的土壤呈碱性,怪不得粮食不肯生长。但碱性的土壤却是茶树的温床。于是,他用自己的青春来改变大山。夏天,他浇水,施肥,沃土;秋天,他剪枝,修枝,发枝。
几载光阴转瞬即逝。清明时分,父亲与我带着山村特有的小筐,上山采茶了,清明茶只能站着采摘,米粒一样大的嫩草一棵树上只能摘十几个,必须“打一枪换一靶”。半天下来,父亲却采摘了一、二斤新鲜茶叶。我望着父亲佝偻的背,掂量着绿意盎然的大山,忽然间明白了:父亲的青春,铭刻在大山的一草一木中,绿得苍茫……
临别前,父亲叮嘱我常回山看看。我几步一回头。父亲,正静静地倚在门槛旁。西沉的落日,在他的身上打出昏黄。此刻,炊烟正从农舍的屋顶袅袅升起,在晚霞中四射,分散,消隐。女人们吆喝孩子的声音此起彼伏。一个男人挑着茶叶从我跟前走过,扁担吱呀吱呀,一路响了过去……
我家的“老顽童”
“妮子,快来帮爷爷瞧瞧这个词儿怎么读!”亮如洪钟的声音第十次传来。
“来了来了!”我高声应和。无奈地瞥了眼桌旁白得晃眼的试卷,我只得先搁下手中微微汗湿的笔。
“真不知道老爷子这次又玩什么花样,唉。”我嘟哝着,一步一拖地朝书房走去。
说起我们家老爷子,偏是个“老不正经”。快七十岁的人了,好歹也是个退休教师,他放着“养鱼晒太阳”的老年生活不享受,偏要赶时髦。穿鲜亮的大红色T恤,穿宽松的萝卜裤,要不是那银光闪闪的白发,还真把他当花季少年呢!
这不,前阵子老爷子又一腔热情的学电脑,说什么要“与时俱进”。这可苦了我哟!从识键盘,到打字再到上网都得手把手教。一遍不行,得十遍二十遍。老爷子戴着老花镜,小鸡啄米似的学得还真上心。怎么着算是出徒了。
“妮子,你快点儿!干嘛呢!”
“来了来了,别急。”我加快了脚步。
“妮子,你看这英文单词怎么读啊?这么多年不操弄,老底子散得差不多了。”只见爷爷眯着眼,用粗大的手指戳着个词急切地望着我。微黄的暖阳透过窗户洒在爷爷镶金边的老花眼镜上,折射出灿然的光星。
“好了,我看看。”接过带着爷爷大手余温的词汇书,一眼便看到了那个用红笔圈出的单词,“听好了,sunshine—阳光,您来一遍。”
接着,爷爷微点着头,嘴唇一上一下地默记了几次,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,那个勤学的少年隐隐可见。
“爷爷,你怎么学起了英文啊?”奈不住好奇,我问道。
爷爷的脸微红了一下,挠了挠头道:“这不咱城市外国人越来越多了,见着他们,一句话不说多没礼貌。爷爷学会了,也好给咱中国人长长脸啊。”
我愣了,只听爷爷继续道:“你们这些小辈常说我‘老不正经’。可老话说‘活到老学到老’。早早地服老了,日子多没滋味!别看爷爷年纪大了,可心却是越活越年轻。保持年轻的心,生活才更有动力嘛。妮子,你说是不?”
望着爷爷,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心永远年轻?对。
“糟了,忘了偷菜了!”爷爷一拍脑袋,忙碌起来。
看着我们家的“老顽童”,我的嘴角自然地上扬了…… 上一页 [1] [2] [3] [4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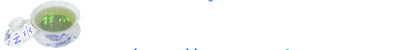
上一篇文章: 2014年高考湖南卷优秀作文:心在哪里 风景就在哪里
下一篇文章: 2014年高考山东省满分作文及点评《关窗·开窗》
|